
量子概念的物理內涵與發展
- Physics Today 專文
- 撰文者:姚岳廷、黃文敏
- 發文日期:2019-07-25
- 點閱次數:2731
量子力學自誕生至今已發展超過上百年,即便如此,物理學家與哲學家仍然持續爭論著「測量(measure)」在量子力學的真正意味。
量子理論剛起步時,科學家開始深入思考量子世界的奧秘之處,如量子糾纏(entanglement)、貝爾不等式(Bell inequality)的違反、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s)、機率的干涉(interference of probabilities)、與量子互文性(quantum contextuality)…等概念。然而,在這思辯過程中提出的許多觀點與理論,現今已被視為資訊處理技術的根基,進而衍生現今物理學上,量子資訊 (quantum information)與量子計算 (quantum computing)這兩大研究領域。由於這些研究領域是經由探討量子物理的根基而生,因此被稱為『應用量子基礎科學(applied quantum foundations)』。這充滿活力的年輕研究領域,不單是由於研究論文都是發表在著名的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RMP)而紅,而是因為它探討著量子物理的根基而著名。
在量子物理基礎的領域中第一篇也是最為深遠的一篇論文可說是理察•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1988) 於1948年提出的論文,「非相對論性量子力學的時空方法」(space-time approach to non-relativistic quantum mechanics)1。費曼在文中利用路徑積分方法(path integral formulation),來區別古典物理和量子物理。
讀者想必在中學時計算過許多機率的題目。假設箱子裡有一顆白球與一顆紅球,我們在蒙著眼的狀況下抽一顆出來紀錄,再放回去,在做了夠多次實驗後,我們會發現抽到紅球與白球的機率各為50%,即我們可藉由「觀測」(在這裡的觀測即為實驗)來獲取系統的「機率」。依據古典物理的想法,即生活中直觀的思考,這件事完全能被接受。但量子理論中,我們卻能根據「執行測量前給定的機率」(即機率波)去計算「實際測量所得之機率」,也就是能「預測」機率,這就非常弔詭的。費曼的解決方式是引入「振幅(amplitude)」來解釋,而他非常清楚的提到:「在我們尚未量測B系統以前,聲明B系統有某些量值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終其一生拒絕接受量子力學的原因了。他曾在與他人討論量子力學時問了一個世紀經典的問題:「只有當我們看月亮時,月亮才在那裡嗎?若我們沒看月亮時月亮就不在那裡?」「看」的動作就是一種量測,所以對於量子力學來說,這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未觀測月亮時,月亮不存在;然而古典力學則認為我們未觀測月亮時,月亮還存在於原本的地點。換句話說,古典力學看到的是物體的「本質(nature)、現實(reality)」;而量子力學看到的是「我們對被觀察事物的最佳描述」,也就是因為這思想上的差異嚴重衝擊到古典力學的世界觀以及日常直覺,使得20世紀初的許多物理學家無法接受量子理論。
隱變量理論, Hidden Variables theory
量子物理挑戰了三百多年來根深柢固的物理學根基,處在一個革命性的年代,必定有許多科學家無法認同新觀點,而埋首於傳統理論的框架中進行修補。當時,這些科學家思考如何盡可能的縮小,因當時的實驗而誕生的量子物理對古典物理直覺的衝擊。他們發現,也許能透過犧牲一些在古典思維中較不重要的直覺,來保留「未執行測量便不能確定系統數值」的想法。這種想法體現在1966年刊登於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的三篇論文2-4,也成為當時「隱變量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而早在1952年,大衛·玻姆(David Bohm)在他的非相對論性量子理論中5,就提出隱變量的想法:「儘管波耳(Niels Bohr)於互補性原理闡明,在不確定性原理之下,粒子位置的不確定性越大,動量的不確定性就越小,反之亦然。但我認為,無自旋的粒子可以被建模為具有預先存在的位置與動量。」的確,多年來人們希望利用隱變量理論來彌補量子世界與古典世界的差異。然而,波姆與傑佛瑞·巴伯(Jeffrey Bub)在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提到,這類新的隱變量模型理論解釋往往取決於科學家的直覺,與他們期待能夠衍生出的新物理3。」
同時在1952年,年輕的約翰·貝爾(John Bell)已經在思考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幾年前所證明之「用隱變量擴展量子理論的不可能性」是否正確,並且提出相關論文2。這篇論文與由波姆與巴伯提出的論文3,4,都認為馮•諾伊曼所提出的理論,只是因為做出過度狹隘的假設而導致得出錯誤的結論。貝爾也進一步提出他的論點:「沒有任何局域性(locality)隱變量的模型能夠符合量子理論的統計結果,換句話說,所有成功的隱變量模型都必須是非局域性的,即具備愛因斯坦著名的EPR(Einstein-Podolsky-Rosen)悖論所述之『鬼魅般的超距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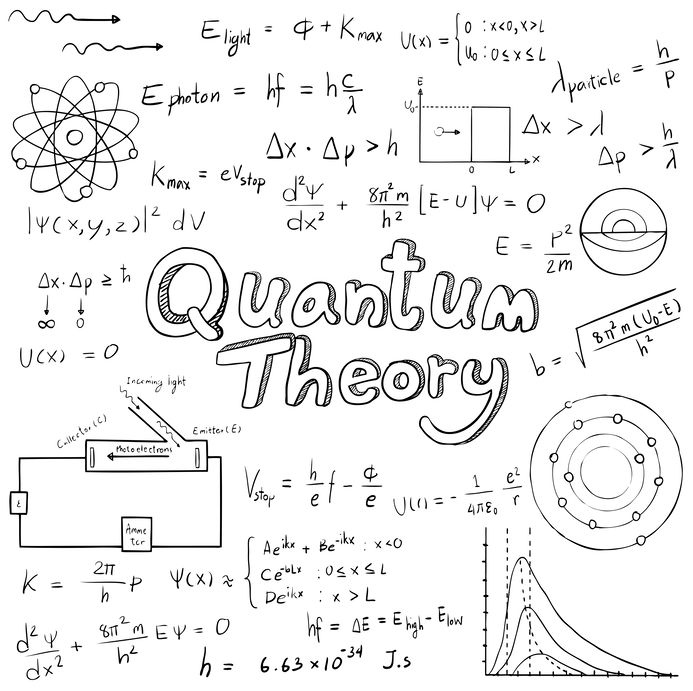
「局域性」是古典概念與量子概念的一個鴻溝,也是科學家持續爭論的一個性質。以古典場論的觀點:一個粒子會受到其周圍空間中的「場」所影響,進而改變其運動狀態,即只有這個粒子周圍的「侷限區域內」的場能使這顆粒子的運動狀況改變。而以相對論的觀點:資訊傳遞的上限為光速,即資訊不可能「瞬間」傳遞,也就是在某段時間內,空間中某點接收到其他點傳來的資訊範圍是有限的(根據光速與經過的時間而定)。這即為古典理論的「局域性」。
反之,在量子理論中存在「量子纏結」的概念,兩顆粒子「纏結」過後,資訊是可以瞬間傳遞的。當你知道一顆粒子的自旋(spin)後,另一顆粒子的自旋也「瞬間」確定;即我們觀測某顆粒子時,另一顆粒子的資訊在我們觀測的瞬間也確定了。另一顆粒子的距離多遠,用光速傳遞資訊需要多少時間都不重要。此為量子理論中的「非局域性」,影響某顆粒子的因素並非只有周圍的場,反而在距離非常遠的地方,亦有愛因斯坦所言之「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影響著這顆粒子的行為。此為量子理論的「非局域性」。
要問古典理論中的「局域性」與「未執行測量的系統具備預先存在(尚未觀測到的)的結果」這兩者孰輕孰重呢 ? 愛因斯坦早已於1948年評論了這個難題:「若我們假設空間中距離遙遠的兩件事物具有某種關聯性,那我們熟悉的物理概念將不復存在。人們亦沒有發現如果沒有清晰的區別,將如何公式化和測試物理定律。6」在貝爾提出他的觀點後的幾年間,這些爭論變得越來越劇烈,也在愛因斯坦發表聲明後的45年後,大衛·梅明(David Mermin)藉由在發表在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的論文中,分析當時新發現的「三粒子 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悖論(three-particle 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 paradox) 」,來全面地陳述此問題的癥結與迫切性7。
「從零開始,It form bit」
除了「在執行測量以前系統可能沒有確定的結果」這種薛丁格的貓的想法,或具有「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的論調,我們有這兩個選擇之外的可能嗎?是否會有其他可能性,只是我們尚未想到?有沒有可能在執行測量以前,這個系統就隱含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在內?由艾略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 1930-1982)於1957年發表於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的論文,首次挑戰哥本哈根詮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來探討了這些看似奇怪的想法所衍伸的問題,而這篇探討「量子理論中多重宇宙理論(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的文章8也成為一篇非常有突破性的論文。可惜的是這篇論文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迴響,而是在這篇論文問世後的50年後,科學界才舉辦研討會,鄭重地看待這個想法。艾略特的想法是假想宇宙可用一個巨大的薛丁格方程(Schrödinger equation)描述,而在任何層面上「測量」都不具備任何意義。唯一有意義的是,物理交互作用(interaction),存在於宇宙這個的漢米爾頓量(Hamiltonian),而這種交互作用導致宇宙持續不斷分支成不同的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s)。這些不同的可能性會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發生,只是我們處於其中一個宇宙並觀測到這個宇宙的現象。
惠勒(John Wheeler, 1911-2008)作為艾略特三世所發表之論文的共同作者,他認為多重宇宙理論最吸引人的地方為它似乎為廣義相對論的量子化(量子重力,quantum gravity)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道路9。但艾略特的解釋並非完全沒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從完全確定的圖像證明量子理論中獨特的機率計算。1957年後,已出現非常多可能的解釋方法,但科學家尚未達成共識。而發表在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的一篇論文,又再一次讓這麼話題浮上檯面。沃傑克•祖瑞克在文章中,以非常全面的角度分析了「量子退相干(Quantum decoherence)」的概念10。量子退相干是指量子系統會與環境(enviroment)產生量子纏結效應,使得量子系統內部的量子狀態會逐漸被環境「吸收、中和」,造成粒子展現出「大環境」的效應,而大環境的效應即為我們巨觀上看到的古典行為。(古典行為與量子行為並非一個微觀一個巨觀,而是在巨觀上不同物體間的交互作用太過複雜,使得只有幾顆粒子才明顯的量子效應變的不明顯)。我們稱此時量子行為因與環境作用而變遷成為古典行為,即為量子效應的「退相干」。在實驗上證明量子纏結時我們經常使用少數原子,因為當原子數目增加時,會更容易與環境纏結產生退相干,而破壞掉這些粒子系統內在的連結,這是量子退相干效應的一個實例。
但惠勒最終還是在艾略特的解釋11中找到許多問題,然而惠勒在討論這些問題中提出的所有觀點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費曼與艾略特進行基礎的研究時,惠勒是他們的博士指導老師,而祖瑞克則是惠勒的博士後研究生,包含近期在黑洞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基普•索恩(Kip Thorne)也是惠勒的學生,由此可見惠勒在物理學界的影響力。在惠勒生命的最後25年內,致力於一種奇特的想法。他拚了命似的想知道「為何需要量子?」而他的猜想是無論答案為何,都應該是「信息理論的顏色(information-theoretic color)」。惠勒認為「一切都是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物質世界的任何物體都處於非常深的底層,而我們所稱的「現實」,是由於我們分析我們提出的問題(理論),以及設備產生的結果(實驗)後產生的,也就是,這是一個參與式的宇宙,物理上所有事物都是我們得到的「信息」所產生的。量子物理並非真正的現實,而是我們對觀察到的現象最好的描述;沒有所謂的量子世界,只有我們如何最佳的描述事物。
實際上,惠勒的觀點對量子資訊領域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本篇的原文作者之一福克斯(Fuchs)非常幸運地接受惠勒的指導,並了解為何惠勒始終如一的將量子態視為一種(主觀的)信息。而這個理論也是首次於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提出12,而後被稱為「量子貝葉斯詮釋(Quantum Bayesianism, QBism)」。將「量子貝葉斯詮釋」與其他詮釋獨立出來的原因,是它仰賴於量子資訊的技術細節來衍伸出費曼的觀點:「對量子理論中機率計算的修改,展現出每次進行測量時,宇宙中都會產生一些新東西。而只有採用量子信息的形式主義才能最清楚的了解它」。
實際上,透過「量子貝葉斯詮釋」的例子,人們可能會好奇是否「量子基礎理論」能夠被「應用量子信息理論」所代替,而這只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而已。不論未來量子基礎領域的研究方向為何,歷史證明了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將會在這個領域持續發表更加深入以及更為深遠的文章。
1. R. P. Feynman, Rev. Mod. Phys. 20, 367 (1948).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20.367
2. J. S. Bell, Rev. Mod. Phys. 38, 447 (1966).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38.447
3. D. Bohm, J. Bub, Rev. Mod. Phys. 38, 453 (1966).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38.453
4. D. Bohm, J. Bub, Rev. Mod. Phys. 38, 470 (1966).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38.470
5. D. Bohm, Phys. Rev. 85, 166 (195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85.166
6. A. Einstein, Dialectica 2, 320 (1948); https://doi.org/10.1111/j.1746-8361.1948.tb00704.x
passage transl. in D. Howard, Stud. Hist. Philos. Sci. Part A 16, 171 (1985), p. 187. https://doi.org/10.1016/0039-3681(85)90001-9
7. N. D. Mermin, Rev. Mod. Phys. 65, 803 (199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65.803
8. H. Everett III, Rev. Mod. Phys. 29, 454 (1957).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29.454
9. J. A. Wheeler, Rev. Mod. Phys. 29, 463 (1957).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29.463
10. W. H. Zurek, Rev. Mod. Phys. 75, 715 (200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75.715
11. J. A. Wheeler, in Quantum Mechanics, a Half Century Later, J. Leite Lopes, M. Paty, eds., Reidel (1977), p. 1.
12. C. A. Fuchs, R. Schack, Rev. Mod. Phys. 85, 1693 (201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5.1693
本文感謝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同意物理雙月刊進行中文翻譯並授權刊登。原文刊登並收錄於Physics Today, January 2019 雜誌內(Physics Today 72, 2, 50 (2019); https://doi.org/10.1063/PT.3.4141);原文作者:Anne Matsuura 、Sonika Johri、Justin Hogaboam 。中文編譯:姚岳廷。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黃文敏,中興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助理教授修訂。
Physics Bimonthly (The Physics Society of Taiwan) appreciates that 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uthorizes Physics Bimonthly to translate and reprint in Mandarin. The article is contributed by Anne Matsuura , Sonika Johri, Justin Hogaboam , and is published on https://doi.org/10.1063/PT.3.41413 The article in Mandarin i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Yueh-Ting Yao, Student of Physic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量子理論剛起步時,科學家開始深入思考量子世界的奧秘之處,如量子糾纏(entanglement)、貝爾不等式(Bell inequality)的違反、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s)、機率的干涉(interference of probabilities)、與量子互文性(quantum contextuality)…等概念。然而,在這思辯過程中提出的許多觀點與理論,現今已被視為資訊處理技術的根基,進而衍生現今物理學上,量子資訊 (quantum information)與量子計算 (quantum computing)這兩大研究領域。由於這些研究領域是經由探討量子物理的根基而生,因此被稱為『應用量子基礎科學(applied quantum foundations)』。這充滿活力的年輕研究領域,不單是由於研究論文都是發表在著名的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RMP)而紅,而是因為它探討著量子物理的根基而著名。
在量子物理基礎的領域中第一篇也是最為深遠的一篇論文可說是理察•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1988) 於1948年提出的論文,「非相對論性量子力學的時空方法」(space-time approach to non-relativistic quantum mechanics)1。費曼在文中利用路徑積分方法(path integral formulation),來區別古典物理和量子物理。
讀者想必在中學時計算過許多機率的題目。假設箱子裡有一顆白球與一顆紅球,我們在蒙著眼的狀況下抽一顆出來紀錄,再放回去,在做了夠多次實驗後,我們會發現抽到紅球與白球的機率各為50%,即我們可藉由「觀測」(在這裡的觀測即為實驗)來獲取系統的「機率」。依據古典物理的想法,即生活中直觀的思考,這件事完全能被接受。但量子理論中,我們卻能根據「執行測量前給定的機率」(即機率波)去計算「實際測量所得之機率」,也就是能「預測」機率,這就非常弔詭的。費曼的解決方式是引入「振幅(amplitude)」來解釋,而他非常清楚的提到:「在我們尚未量測B系統以前,聲明B系統有某些量值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終其一生拒絕接受量子力學的原因了。他曾在與他人討論量子力學時問了一個世紀經典的問題:「只有當我們看月亮時,月亮才在那裡嗎?若我們沒看月亮時月亮就不在那裡?」「看」的動作就是一種量測,所以對於量子力學來說,這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未觀測月亮時,月亮不存在;然而古典力學則認為我們未觀測月亮時,月亮還存在於原本的地點。換句話說,古典力學看到的是物體的「本質(nature)、現實(reality)」;而量子力學看到的是「我們對被觀察事物的最佳描述」,也就是因為這思想上的差異嚴重衝擊到古典力學的世界觀以及日常直覺,使得20世紀初的許多物理學家無法接受量子理論。
隱變量理論, Hidden Variables theory
量子物理挑戰了三百多年來根深柢固的物理學根基,處在一個革命性的年代,必定有許多科學家無法認同新觀點,而埋首於傳統理論的框架中進行修補。當時,這些科學家思考如何盡可能的縮小,因當時的實驗而誕生的量子物理對古典物理直覺的衝擊。他們發現,也許能透過犧牲一些在古典思維中較不重要的直覺,來保留「未執行測量便不能確定系統數值」的想法。這種想法體現在1966年刊登於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的三篇論文2-4,也成為當時「隱變量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而早在1952年,大衛·玻姆(David Bohm)在他的非相對論性量子理論中5,就提出隱變量的想法:「儘管波耳(Niels Bohr)於互補性原理闡明,在不確定性原理之下,粒子位置的不確定性越大,動量的不確定性就越小,反之亦然。但我認為,無自旋的粒子可以被建模為具有預先存在的位置與動量。」的確,多年來人們希望利用隱變量理論來彌補量子世界與古典世界的差異。然而,波姆與傑佛瑞·巴伯(Jeffrey Bub)在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提到,這類新的隱變量模型理論解釋往往取決於科學家的直覺,與他們期待能夠衍生出的新物理3。」
同時在1952年,年輕的約翰·貝爾(John Bell)已經在思考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幾年前所證明之「用隱變量擴展量子理論的不可能性」是否正確,並且提出相關論文2。這篇論文與由波姆與巴伯提出的論文3,4,都認為馮•諾伊曼所提出的理論,只是因為做出過度狹隘的假設而導致得出錯誤的結論。貝爾也進一步提出他的論點:「沒有任何局域性(locality)隱變量的模型能夠符合量子理論的統計結果,換句話說,所有成功的隱變量模型都必須是非局域性的,即具備愛因斯坦著名的EPR(Einstein-Podolsky-Rosen)悖論所述之『鬼魅般的超距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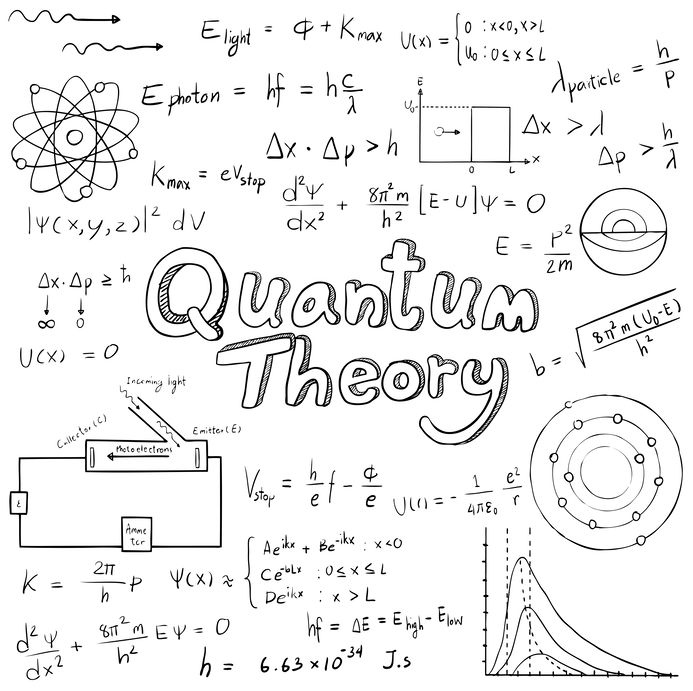
「局域性」是古典概念與量子概念的一個鴻溝,也是科學家持續爭論的一個性質。以古典場論的觀點:一個粒子會受到其周圍空間中的「場」所影響,進而改變其運動狀態,即只有這個粒子周圍的「侷限區域內」的場能使這顆粒子的運動狀況改變。而以相對論的觀點:資訊傳遞的上限為光速,即資訊不可能「瞬間」傳遞,也就是在某段時間內,空間中某點接收到其他點傳來的資訊範圍是有限的(根據光速與經過的時間而定)。這即為古典理論的「局域性」。
反之,在量子理論中存在「量子纏結」的概念,兩顆粒子「纏結」過後,資訊是可以瞬間傳遞的。當你知道一顆粒子的自旋(spin)後,另一顆粒子的自旋也「瞬間」確定;即我們觀測某顆粒子時,另一顆粒子的資訊在我們觀測的瞬間也確定了。另一顆粒子的距離多遠,用光速傳遞資訊需要多少時間都不重要。此為量子理論中的「非局域性」,影響某顆粒子的因素並非只有周圍的場,反而在距離非常遠的地方,亦有愛因斯坦所言之「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影響著這顆粒子的行為。此為量子理論的「非局域性」。
要問古典理論中的「局域性」與「未執行測量的系統具備預先存在(尚未觀測到的)的結果」這兩者孰輕孰重呢 ? 愛因斯坦早已於1948年評論了這個難題:「若我們假設空間中距離遙遠的兩件事物具有某種關聯性,那我們熟悉的物理概念將不復存在。人們亦沒有發現如果沒有清晰的區別,將如何公式化和測試物理定律。6」在貝爾提出他的觀點後的幾年間,這些爭論變得越來越劇烈,也在愛因斯坦發表聲明後的45年後,大衛·梅明(David Mermin)藉由在發表在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的論文中,分析當時新發現的「三粒子 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悖論(three-particle 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 paradox) 」,來全面地陳述此問題的癥結與迫切性7。
「從零開始,It form bit」
除了「在執行測量以前系統可能沒有確定的結果」這種薛丁格的貓的想法,或具有「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的論調,我們有這兩個選擇之外的可能嗎?是否會有其他可能性,只是我們尚未想到?有沒有可能在執行測量以前,這個系統就隱含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在內?由艾略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 1930-1982)於1957年發表於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的論文,首次挑戰哥本哈根詮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來探討了這些看似奇怪的想法所衍伸的問題,而這篇探討「量子理論中多重宇宙理論(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的文章8也成為一篇非常有突破性的論文。可惜的是這篇論文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迴響,而是在這篇論文問世後的50年後,科學界才舉辦研討會,鄭重地看待這個想法。艾略特的想法是假想宇宙可用一個巨大的薛丁格方程(Schrödinger equation)描述,而在任何層面上「測量」都不具備任何意義。唯一有意義的是,物理交互作用(interaction),存在於宇宙這個的漢米爾頓量(Hamiltonian),而這種交互作用導致宇宙持續不斷分支成不同的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s)。這些不同的可能性會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發生,只是我們處於其中一個宇宙並觀測到這個宇宙的現象。
惠勒(John Wheeler, 1911-2008)作為艾略特三世所發表之論文的共同作者,他認為多重宇宙理論最吸引人的地方為它似乎為廣義相對論的量子化(量子重力,quantum gravity)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道路9。但艾略特的解釋並非完全沒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從完全確定的圖像證明量子理論中獨特的機率計算。1957年後,已出現非常多可能的解釋方法,但科學家尚未達成共識。而發表在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的一篇論文,又再一次讓這麼話題浮上檯面。沃傑克•祖瑞克在文章中,以非常全面的角度分析了「量子退相干(Quantum decoherence)」的概念10。量子退相干是指量子系統會與環境(enviroment)產生量子纏結效應,使得量子系統內部的量子狀態會逐漸被環境「吸收、中和」,造成粒子展現出「大環境」的效應,而大環境的效應即為我們巨觀上看到的古典行為。(古典行為與量子行為並非一個微觀一個巨觀,而是在巨觀上不同物體間的交互作用太過複雜,使得只有幾顆粒子才明顯的量子效應變的不明顯)。我們稱此時量子行為因與環境作用而變遷成為古典行為,即為量子效應的「退相干」。在實驗上證明量子纏結時我們經常使用少數原子,因為當原子數目增加時,會更容易與環境纏結產生退相干,而破壞掉這些粒子系統內在的連結,這是量子退相干效應的一個實例。
但惠勒最終還是在艾略特的解釋11中找到許多問題,然而惠勒在討論這些問題中提出的所有觀點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費曼與艾略特進行基礎的研究時,惠勒是他們的博士指導老師,而祖瑞克則是惠勒的博士後研究生,包含近期在黑洞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基普•索恩(Kip Thorne)也是惠勒的學生,由此可見惠勒在物理學界的影響力。在惠勒生命的最後25年內,致力於一種奇特的想法。他拚了命似的想知道「為何需要量子?」而他的猜想是無論答案為何,都應該是「信息理論的顏色(information-theoretic color)」。惠勒認為「一切都是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物質世界的任何物體都處於非常深的底層,而我們所稱的「現實」,是由於我們分析我們提出的問題(理論),以及設備產生的結果(實驗)後產生的,也就是,這是一個參與式的宇宙,物理上所有事物都是我們得到的「信息」所產生的。量子物理並非真正的現實,而是我們對觀察到的現象最好的描述;沒有所謂的量子世界,只有我們如何最佳的描述事物。
實際上,惠勒的觀點對量子資訊領域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本篇的原文作者之一福克斯(Fuchs)非常幸運地接受惠勒的指導,並了解為何惠勒始終如一的將量子態視為一種(主觀的)信息。而這個理論也是首次於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中提出12,而後被稱為「量子貝葉斯詮釋(Quantum Bayesianism, QBism)」。將「量子貝葉斯詮釋」與其他詮釋獨立出來的原因,是它仰賴於量子資訊的技術細節來衍伸出費曼的觀點:「對量子理論中機率計算的修改,展現出每次進行測量時,宇宙中都會產生一些新東西。而只有採用量子信息的形式主義才能最清楚的了解它」。
實際上,透過「量子貝葉斯詮釋」的例子,人們可能會好奇是否「量子基礎理論」能夠被「應用量子信息理論」所代替,而這只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而已。不論未來量子基礎領域的研究方向為何,歷史證明了現代物理學評論期刊將會在這個領域持續發表更加深入以及更為深遠的文章。
1. R. P. Feynman, Rev. Mod. Phys. 20, 367 (1948).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20.367
2. J. S. Bell, Rev. Mod. Phys. 38, 447 (1966).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38.447
3. D. Bohm, J. Bub, Rev. Mod. Phys. 38, 453 (1966).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38.453
4. D. Bohm, J. Bub, Rev. Mod. Phys. 38, 470 (1966).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38.470
5. D. Bohm, Phys. Rev. 85, 166 (1952)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85.166
6. A. Einstein, Dialectica 2, 320 (1948); https://doi.org/10.1111/j.1746-8361.1948.tb00704.x
passage transl. in D. Howard, Stud. Hist. Philos. Sci. Part A 16, 171 (1985), p. 187. https://doi.org/10.1016/0039-3681(85)90001-9
7. N. D. Mermin, Rev. Mod. Phys. 65, 803 (199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65.803
8. H. Everett III, Rev. Mod. Phys. 29, 454 (1957).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29.454
9. J. A. Wheeler, Rev. Mod. Phys. 29, 463 (1957).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29.463
10. W. H. Zurek, Rev. Mod. Phys. 75, 715 (200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75.715
11. J. A. Wheeler, in Quantum Mechanics, a Half Century Later, J. Leite Lopes, M. Paty, eds., Reidel (1977), p. 1.
12. C. A. Fuchs, R. Schack, Rev. Mod. Phys. 85, 1693 (2013). https://doi.org/10.1103/RevModPhys.85.1693
本文感謝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同意物理雙月刊進行中文翻譯並授權刊登。原文刊登並收錄於Physics Today, January 2019 雜誌內(Physics Today 72, 2, 50 (2019); https://doi.org/10.1063/PT.3.4141);原文作者:Anne Matsuura 、Sonika Johri、Justin Hogaboam 。中文編譯:姚岳廷。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黃文敏,中興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助理教授修訂。
Physics Bimonthly (The Physics Society of Taiwan) appreciates that 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uthorizes Physics Bimonthly to translate and reprint in Mandarin. The article is contributed by Anne Matsuura , Sonika Johri, Justin Hogaboam , and is published on https://doi.org/10.1063/PT.3.41413 The article in Mandarin i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Yueh-Ting Yao, Student of Physic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